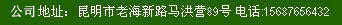|
隐藏的锁链:周城传说故事与女性社会地位变迁——云南大理白族村的人类学考察 杨雪 摘要: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在“受压迫的女性”前提下探讨女性的自由与解放,而流传于大理周城白族村贬抑女性的母猪龙传说、捆锁女性的本主故事和限制女性的关帝庙禁忌,在近百年来的变化形貌中反映出,“受压迫的女性”一说已不能适应当前女性社会地位的现状。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与其说是外在的传统与社会观念限制着女性自由,毋宁说是女性主动将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诉求,“自我束缚的女性”才是限制女性发展的隐藏的锁链。 关键词:白族女性;传说故事;女性社会地位;外在规范;内在诉求 前言在多民族聚居的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1]因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与受汉文化熏陶下的女性不同。自汉武帝在云南设立益州郡,中原文化虽一直影响着云南各民族,但直至明清时期云南被纳入统一王朝的政治版图,这种影响才广泛显现。随着行省制度、土司制度、封建地主经济在云南的确立,再加上汉族的大规模移民,汉文化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乐教化的影响,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转折。从唐代云南妇女“处子霜妇出入无禁”,到明清时“诸蛮扬贞风”和“列女群”的出现,“各民族妇女的地位和存在价值也在以汉文化为主导的背景中,走向从属”[2]。白族尤其受汉文化影响较深,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爬梳,沈海梅从史学的角度得出结论:“白族婚姻及同妇女生活有关的习俗在明清时期发生的变化最为剧烈”[3]。 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云南大理喜洲镇的“民家人”(五十年代被认定为白族)研究中,更具体地描绘了当时白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喜洲镇,人们强调父子关系而贬低夫妻关系,男性完全优先女性,不仅丈夫在妻子之上,就连兄弟亦是优先于姐妹的。“一个女人必须服从于她的父亲、丈夫、婆婆。当丈夫去世后,她甚至必须服从她的儿子。她唯一的办法便是等候时机,将心中的不平发泄于女儿,或是儿媳,或是那些与她无亲无故,但碰巧妨碍她的人身上。……喜洲镇的妇女,其地位是被动的、服从的。”[4]许烺光认为“民家人”在强调父子合一的大家庭理想下,限制女性进行自我改善的枷锁多于男性。 沈海梅和许烺光都将白族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归因于历史中受外在制度和观念的禁锢与建构,这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观点是一致的。这种观点认为“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5],并且女人并不是生为女人,而是被“教育和习俗”塑造为“女人”,附属于男性存在[6]。从这一观点出发,一百多年来,许多致力于男女平等的志士仁人为争取妇女的选举权、社会和经济地位平等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并卓有成效。随着社会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的转变,世界范围包括中国在内的女性主义理论方向转至对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和男权制的批判[7],“受压迫的女性”的前提论点仍然是学者们为女性争取自由所挥舞的冲锋大旗。 笔者根据在喜洲镇辖区的周城村[8]的田野调查发现,作为民众对自身生存与生活景况的集体再表述,在本村流传的三个传说故事及其在近百年来流传中的变化形貌,向我们揭示出相较于当地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社会观念对女性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贬抑女性的母猪龙故事和被捆绑的两位娘娘的传说在渐渐消失或遭遇改写,从侧面体现出“受压迫的女性”一说已不能适应当前背景下女性社会地位的现状。但仍行之有效的关帝庙的禁忌则反映出,在女性地位普遍提高的今天,“自我束缚的女性”才是限制女性发展的隐藏的锁链。 一、母猪龙传说:被贬抑的女性母猪龙的传说在云南大理地区流传较广,因地域不同,故事的情节发展随之不同,如洱海边的村庄一般将母猪龙看作洱海里面的生物,会引发洪灾。而在苍山脚下的周城,母猪龙的故事主要与山上的泥石流以及女性的作风有关。据YZY老人(80岁)讲述,母猪龙是由一名葬在周城西面鼓山上的孕妇所变。“这个孕妇呢,她是女的,修行了一千多年,变成了一个母猪龙。龙嘛有好多种,这个是属于妖怪里面的龙。”(YZY访谈记录) 母猪龙虽然同样是龙,但由死去孕妇所变,所以属于妖怪。传说在一百多年前,母猪龙有两次作乱,在周城造成了泥石流和妇女作风的“败坏”:“母猪龙嘛她得作怪。你们是叫泥石流是吧,我们这不叫,我们叫塌沙。泥山泥石冲出一股水,把周城的土地田地都一冲两半。这小口现在还在,我们喊它断田沟,在南登后面。……母猪龙是个妖怪,周城的妇女,这些妇女的作风也相当坏了。有母猪龙占了上风了,统治是她了嘛。所以一般是男人追求女人,现在是女人去拉男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衣服嘛穿着红红绿绿的……隔现在多年。所以,周城的风俗习惯很不行了,没办法了。所以就,村子里也想不出办法,这些女人是这么风流,这些女人是这个乱搞。”(YZY访谈记录) 传说当时周城村的段凌云、杨上培[9]等知识精英为了压制女性的这种风气,便规定妇女不能穿的红红绿绿,倘若哪个人穿的“妖里妖怪”就罚款,把衣服剥下来撕烂、烧掉,但仍压不下去。后来,他们便在鼓山上修了一座塔,名为“镇文静”,意思是镇住母猪龙,使她变得文明安静。塔建成后周城女性的作风的确有所缓和,但母猪龙不死,妖风邪气仍在继续。第二次作怪在下街百多十米处,依旧是“塌沙”(泥石流)。这次周城村民在第一座塔的旁边又修了一座塔,叫“狡笔川”,意为“把这个母猪龙,这个狡龙,把她的鼻子穿起来,把这个字(指‘鼻’)改成这个字(指‘笔’),周城是很讲文明的,狡笔川。狡笔川这个塔整起来以后,从此以后,社会就平稳了,一样都没有了。”(YZY访谈记录) 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把这两座塔挖倒,周城的风俗习惯又“坏起来了”。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我们修了电影院,现在不放了,(现在)个个都有电视嘛,(以前)晚上男男女女都去那边,有的去看电影,有的在外边玩。大树底下,花坛旁边,小伙子如果是靠在那个地方,三五个小姑娘就来了,那个时候作风就很坏,那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哎,八十年代。”(YZY访谈记录) 直到九十年代,村子为了通电在山上修建了钢架塔。“电力公司拉了一股高压线,可能是三四万伏吧,……从鼓山上拉过去,现在还在,(这边)钢架竖上一个,(那边)钢架竖上一个,这个钢架比这个塔更好一点。它是带阳气,(虽然)两个塔去了,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周城的风俗习惯很坏,(但是)自从这个钢架搞起来了现在又好一点。现在周城妇女稍微好一点,现在作风比过去好一点。母猪龙死不死不知道,她不捣乱就是。”(YZY访谈记录) 如今,母猪龙的故事早已被人们淡忘,母猪龙作乱与否与女性行为作风的好坏不再相关,只与自然灾害有关。ZSJ老人(84岁)认为现在没有妖怪:“哪有什么妖怪嘛,这个是传说,一样没有看过嘛。”母猪龙只是“地皮下一种大动物了嘛,可以在地底下造反,可以整那个泥石流滑坡,这些就是母猪龙干的。”(ZSJ访谈记录)至于以前社会上要求女人要听男人的,不能穿得花花绿绿,他认为“意思就是女的要守家份,规规矩矩,要老实做人,衣服这些要素雅。现代嘛你穿什么哪个管得了,是不是。”(ZJS访谈记录) 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一种隐喻的指涉:女性的角色与妖怪母猪龙是等同的。一方面,在传说的叙事中,妖怪母猪龙占上风,就会带来自然灾害,社会上女性作风变坏;妖怪母猪龙被镇住,女性作风就变好,自然也和谐。女性所谓的“坏”的作风,包括穿得花花绿绿和“妖里妖怪”,以及主动追求男性等,这与传统社会中所提倡的“好”的作风——女性应被动顺服的观念——是不合的。倘若女性不合传统,那一定是妖怪占了上风,并有相应的天灾暗示,自然秩序与社会中所提倡的女性作风相互映照。另一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母猪龙作乱的时间,恰好与历史上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关键期暗合。根据传说,前两次母猪龙占上风的时间是距今多年,正是民国时期,这期间全国普遍兴起了争取身体上与服饰上自由的妇女解放运动,而周城传统士绅对此的反应是明令限制妇女的着装,压制女性“坏”的作风。随后女性被认为“又不得了”是文革以后,尤其是八十年代,女性主动追求男性,“作风就很坏”。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白族女性逐渐拥有婚姻自主权的时期。最后,母猪龙的故事渐渐不再流传,周城能讲述这一故事的老人大都已八十岁以上了,大部分人都不再认同妖怪一说,母猪龙与女性作风之间的关联断裂,也显示出社会观念对女性突破传统礼教行为的接纳,女性逐渐掌握了婚姻恋爱及衣着服饰等生活上的自主权。 二、两位娘娘的故事:被捆锁的女性母猪龙故事因社会观念的变迁而渐渐不再流传,而本主杜朝选[10]与两位娘娘的故事在周城几乎人尽皆知,其中李星华于年记录整理的“蝴蝶泉”故事[11]是现今流传较广的一种版本。但在田野调查期间,笔者不断地听说另外一种传说版本,这两种版本之间的区别,显示了女性地位变化的微妙之处。 故事的主人公是海东永胜县一个名叫杜朝选的猎人,在周城附近的山林打猎时,听到村民痛哭的声音,得知这一带的深山中有个会变人形的蟒蛇,每年都要百姓供奉一对童男童女,否则就全村遭殃。眼看周城村民苦不堪言,杜朝选便独自到深山中要除灭蟒蛇。经过一番大战之后,蟒蛇负伤逃走,杜朝选紧追不舍,在一个小溪边看见两位女子在洗血衣,询问后方知这两位女子是被蟒蛇掳来,现今蟒蛇受伤休息,它一般大睡是七天七夜,小睡是三天三夜,此时蟒蛇正在大睡。两名女子将杜朝选带入蟒蛇洞,帮助他盗走蟒蛇的宝剑,杜朝选趁此挥剑将蟒蛇砍死,剑也因此断成两段。而被他救出的两名女子为报救命之恩,主动提出要做他的妻子,但杜朝选认为自己除蟒是为民除害,拒绝了两位女子的请求,转身到山上打猎去了。两名女子追赶不上,在一个龙潭边歇脚,千愁万恨,没法解开,便跳入潭中身亡。杜朝选闻之十分后悔,也跳入潭中自尽,他们三个死后化作三只蝴蝶,所以蝴蝶泉边的蝴蝶总是两只在前面飞,一只在后面追。周城人民为了感激杜朝选,便将它尊为本主。现在的北本主庙,也称为“灵帝庙”,供奉的主神就是杜朝选和这两位娘娘。 这一版本的故事中,杜朝选斩杀恶蟒,救周城百姓脱离困境,婉拒两位姑娘的求婚,后追随她们跳入潭中化作蝴蝶。他的忠肝义胆并侠骨柔肠形象跃然纸上,令人既敬佩又惋惜。但笔者在调查期间却听到与之相异的版本,如前述的YZY就认为并非是两位娘娘主动向杜朝选求婚,而是杜朝选“杀夫霸妻”,两位娘娘是被动的。“我说是杜朝选向她们两个求婚,她们两个不干,我是有根据的。杜朝选杀了蟒蛇,这个就喊他‘杀夫’。他又把它两个婆娘拿来,这叫‘霸妻’。(他们认为)这个不好,把它改成就是这两个姑娘就(说):大哥我们做你的媳妇。改成这样,提高一下杜朝选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组的想法就是这样。周城有些人写也是这样。”(YZY访谈记录) YZY所说的根据是长辈讲给他的故事,以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本主庙中两位娘娘的塑像。“在解放以前,大娘娘手被铁链子拷起,下面垂着一把锁。五六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大娘娘的形象就是如此,老人们都记得很清楚。年的时候把它销毁掉了,年、年重新整,现在重新塑的大娘娘手是缩到袖子里面去的,上面没有铁链子了。”[12]据他所说,他的祖父辈们流传下来的说法就是杜朝选向两位娘娘求婚,二娘娘愿意就跟他生了个小娃娃,大娘娘不愿意,所以她的双手被锁链捆起来。大娘娘之前的塑像是带着锁链,村里其他老人对此也都有印象,“大娘娘对杜朝选有点心不热,可能是不喜欢他,杜朝选刻给她一把锁,挂在她的脖子上,后来她也没有意见。二娘娘有个娃娃,就一心一意地跟杜朝选过”[13]。 徐嘉瑞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也有相似观点。他记载的故事并未提及是两位女子向杜朝选求婚还是杜朝选追求两位女子,只是说“两个女子,就做了他的娘娘。”[14]但作者后面的评论很耐人寻味,他认为这个传说故事与屈原在《天问》一文中所悲叹的是同一类的事。屈原感慨后羿射杀河伯之后,将河伯所强占的雒嫔再据为己有一事,呼天问之,悲叹正义何在。可见徐嘉瑞所了解的杜朝选与两位娘娘的故事应与YZY所说“杀夫霸妻”一事相符。 此外,与此相关的还有朱炳祥在周城搜集到的一种故事版本:“大娘娘嫁了杜朝选,二娘娘认为一夫多妻不好,不愿意。杜朝选领她们回永胜时,路过蝴蝶泉边,二娘娘就跳进龙潭里,化成了蝴蝶。龙潭就变成了现在的蝴蝶泉。”[15]虽然这一情节与笔者所搜集到的略有不同,反抗男性求婚的对象变成了二娘娘,反抗的原因涉及到现代国家的婚姻政策对故事流传的影响,不过相似的是,它们所表述的故事结构都是杜朝选要两个姑娘做他的妻子,一名女子顺从,另一名女子反抗。 村民们将杜朝选奉为周城本主的时间是公元年,他和两位娘娘的塑像被供于灵帝庙中,YZY等人都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大娘娘塑像是有锁和锁链的。七八十年代,村民们重塑在文革中遭毁的本主神像,其他塑像基本没有变化,唯独大娘娘的塑像有改动。笔者曾仔细观察过灵帝庙中三人的塑像,庄严威武的杜朝选手持斩蟒的断剑,其右侧的二娘娘身旁偎依着一个小男孩,而其左侧的大娘娘双手以交叠的姿势放在胸前,本应裸露在外的双手被一方绿手帕盖住,脸上带着蒙娜丽莎般的微笑,仿佛暗示着那看不到的锁链仍隐藏在帕子下。 在这一故事中,杜朝选杀蟒蛇是不变的母题,但杜朝选与两位娘娘之间的情节发展却有两种类型:“杜朝选强娶二女”说和“二女求爱杜朝选”说。虽然很难精确追溯哪一种较久远,不过比照文史资料、村民对传说的记忆以及庙中三人的塑像来看,“杜朝选强娶二女”应是更早的传说版本,但显然后者成为集体记忆的主流,更为人们所熟知。 对比这两种不同叙事中男性与女性的形象,可以发现改写前后女性地位的变动。“二女求爱杜朝选”说是典型的英雄救美故事,男性既勇武正直又不趁人之危,女性是英雄的爱慕者,主动向男性求婚,在遭拒后仍矢志不渝最终跳潭殉情,而三人化蝶的结尾又使这一浪漫传说更显隽永动人。相较之下,“杜朝选强娶二女”说所描述的男性与女性则更具现实和悲剧色彩。其中,男性既有斩杀恶蟒的勇武形象,也有霸占女性的不光彩行为,而作为受害者的女性在面对男性的强威时,虽有拒绝服从的不屈,也有逆来顺受的软弱。之所以将两位姑娘被迫嫁给杜朝选这一情节宣传为主动追求杜朝选,并且重修在“文革”中遭毁的神像时去掉大娘娘手上的锁链,村民认为是政府部门对封建思想的把关。作为现代语境下的英雄杜朝选,不再被允许有“霸妻”行为,而女性不服从男性会被拷上锁链一事在现代社会中也不能被接受,这一改写从反向证明了国家对女性的尊重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在前述母猪龙故事中不被认可的女性主动追求男性的情况,反而成为这一版本的主要情节,其中的浪漫和哀伤,更是为传说所在地蝴蝶泉[16]平添了许多诗意,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三、关帝庙的禁忌:自我束缚的女性母猪龙传说的淡出与二位娘娘故事的改写,体现出束缚女性的外在制度与观念在逐渐改变,而周城关帝庙的故事,关涉着女性实际生活中的行为禁忌,仍然在当地行之有效。关公崇拜在中国民间信仰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大理白族地区也不例外,而在周城,却一直流传着关公不喜欢女人的故事,女性不得入内关帝庙成为周城独特的地方禁忌。 周城村的关帝庙,也称武庙,于公元年修建,作为南侧殿附属于当时已初具规模的龙泉寺。建成于明朝宣德年间的龙泉寺,初时只是一座二层三开间品字形结构大殿,是典型的“三教合一”的寺宇:一层楼的正殿主要供奉如来、孔子与太上老君以及观音老祖,旁边塑有大黑天神与达摩祖师,二层楼独塑玉皇大帝,也被单独称为“玉皇阁”。关帝庙建成18年后,正殿以北又修建了供奉文昌帝君的文庙,后陆续建成南北两座分别供奉观音三姐妹及三官大帝的厢房。 龙泉寺中,除了全村村民都敬畏但很少拜祭的玉皇阁,最具权力与威严的殿宇就是关帝庙。“周城最崇拜的就是关公了。他是对国以忠,对人以义,对事以仁,作战以勇,他是忠义仁勇。对于关公,佛教说关公是佛教的人,道教说关公是道教的人。喇嘛教也是这样,说是他们的人,都是尊重关公。我们周城尊重他是尊重他忠义仁勇。本主接出来以后,第一个节目是跳财神,第二个节目必须是跟关公有关的节目,其他的节目就随便了。”[17]在过去,凡遇攸关全村命运的重大事件,周城村民就在关帝庙中举行隆重的扶乩占卜活动,向关公“支沙盘”求问。前述灵帝庙中供奉的斩蟒猎人杜朝选本主的名字和圣号都是村民“请”关公“明示”所知的,由此可见关公在周城神灵信仰中的地位。 然而,这样有威望的关帝庙,周城最热心拜神的女性却不能进去祭拜。当地习俗,遇有家中孩子考大学或求平安时要到龙泉寺敬神,一般都是女性负责,她们会逐一拜祭寺庙中供奉的所有神祗,要亲自在神像前呈上贡果,倒上茶水,献上功德钱,并磕头作辑。而对于关帝庙,村中的女人们只是远远地在庙外台阶处端着供品作辑,跪下磕头,绝对不会上去庙里。即便是打破传统加入洞经会[18]的女性会员,遇有需要在关帝庙上会弹经的会期时,她们也只坐在庙外的墙根处弹奏乐器,或者在门口叩拜,而不敢像男性会员那样随意进入庙中。女人不能进关帝庙这一故事在人们心中的禁忌力,由此可见一斑。 女人为什么不能进关帝庙?笔者在调查时发现与此相关的两个故事。 村中的老年男性告诉笔者,是因为传说关帝不喜欢女人,女人影响关帝的“义”。南方广莲池会[19]的副会长YJ说:“关圣,传说就是女人不能进去。这个我们也莫名其妙,老一代传下来的就是女的不能进去。女人要是进去会得病。他们说是他怪,看到女的他不喜欢。”(YJ访谈记录)这个传说缘于《三国演义》[20],据洞经会会长LYZ讲述:“就是关公夜看春秋了,它有这样的故事是不是。他宁愿千里走单骑,刘备在一方,他(刘备)的两个妻子失散了,然后关公红脸了嘛,在战火当中,过五关把她们带回来,带回来以后,曹操试试他(关羽)的心了嘛,然后二位皇嫂在一个地方,他(关羽)在外边守着,晚上就是夜看春秋了嘛,守着刘备的妻子了嘛。他的义就义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见不得女的,女的进不得那边。”(LYZ访谈记录)在忠义与女人之间,关羽选择了前者:“所以他(关羽)对女人就是,意思就是想拉他下水的这种做法到非常反感。他死了,以后人家就把他说成,他不喜欢女人。”(DJC访谈记录) 同时,村民们还记得一个女人因触犯了关帝庙禁忌而死去的故事。早些年,一个怀孕的妇女从龙泉寺经过,当时关帝庙正对着的龙泉寺南侧门没有关上,她被关帝“看见”,不久就奇怪身亡,连同腹中的婴儿一起死去,自此以后龙泉寺南侧门便被锁上,只留正门和文庙所对着的北侧门供人进出(年8月4日田野日志)。就这一事情的真实性,笔者曾询问过许多村民,退休的小学老师ZP(82岁)与前述YZY老人(80岁)都说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发生在二三十年前,他们以前认识这个女人的家人,也有人认为“不可能,一见到就死,哪有这种道理”,大多数人对此不置可否(YZY访谈记录、田野日志、DJC访谈记录)。 然而,有意思的是,不敢进入关帝庙的村中女性却从未向笔者讲述过关帝不喜欢女人的传说,对一个怀孕妇女进关帝庙后死去的故事倒是有所耳闻,但女性更常见的看法是因为“他们说去不得”、“去了会得病”或者“会肚子疼”。一位莲池会老妈妈YYJ说“就怕进去肚子疼了”,当笔者询问是否有人进去过然后肚子疼时,她说没有,“但是不能去,不能看。”她告诉笔者洞经会的女性会员在关帝庙上会时,也只是坐在旁边,不直接面对关帝,“她们自觉了嘛,自觉不能去”(0803YYJ、GDS访谈记录)而她的老倌GDS在一旁插话:“这种事情属于一种心理作用,是自己尊重自己,自己爱护自己。”洞经会的YJK阿姨告诉笔者的确如此:“我们很少去那里(我:很少去?那你们演奏的时候?)坐在外面(我:也不进去?会长说了不让你们进去吗?)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不要进去。(我: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YJK访谈记录) 笔者在龙泉寺调查期间,曾看见一个11岁的小女孩被她的姑姑严肃警告不能去关帝庙(田野日志),自己也多次被村里的老妈妈们善意提醒不要进去关帝庙,否则会得病:“阿奶说给你,那里女的去不得,女的不能去。(我:去不得?为什么啊?)去了会得病。(我:啊,我去过)去过嘛晓不得嘛不要怕,晓不得嘛不有罪。晓得去有罪了,晓不得嘛罪不有。(我:那我站在外面可以吗?)恩恩,站外面可以。”(LQS访谈记录) 但村里的老倌倌对此却反应不同,对他们来说,这一禁忌并非如此严格。有老人说也有觉得自己很“干净”的老妈妈进去关帝庙:“话粗理正哈,说话说的难听,但是道理正。年纪轻的女人,她有月经,大一点的人她身上怀孕,这一种就是不干净的人,走拢关圣人不行,走到玉皇大帝那里也不行。所以老妈妈,很干净的人,她们还是走的,她们不怕。”(YZY访谈记录,DJC访谈记录)笔者在调查时并未发现有这样的老妈妈,但当提到自己曾进去过关帝庙时,上文讲述关帝不喜欢女人传说的LYZ与YJ等人的回答却是:“不怕,人嘴巴讲成嘛,弯也得,直也得,讲是这样讲,进去也就进去了”,“你们本心无愧这个不怕”,“小娃娃不怕”,“你是大学(生)了嘛”(LYZ访谈记录,YJ访谈记录,0803YYJ、GDS访谈记录,0804HS访谈记录)。 对于关帝不喜欢女人的传说,村中的很多男性也颇不认同。一名某姓氏的宗族长SBT说:“他们说哎呀,这个他(关羽)见不得女的,女的上去以后,好像得罪他这个忠义的义嘛。讲忠义,就是封建的思想。他妈还不是女人。是不是?这是自己约束自己。”(SBT访谈记录)洞经会会友YZS也有此看法,认为并不是关帝歧视女人,是女人自己歧视自己:“这个是我们这边兴,过去有个成语,就是说他(关羽)对妇女好像有点歧视。但心理面不是歧视,但是他的相貌,吓人的样子,女的想法就是否定关圣,但他心理面是没有反对她的意思,是他母亲把他生成这个样子。但女人懂的多,自己歧视自己,就看着他的这张脸,红通通的,害怕,就不敢面对他。”(YZS访谈记录) 并且,也有极少数女性认为即便进去了关帝庙,也没有什么关系。YZL大妈(58岁)因为喜爱弹奏乐器,在年首开先河加入以前只有老年男性参加的洞经会,成为周城第一名洞经会女性会员:“他们是说女的不要进去那里,他(关羽)不要瞧着女的。但是我以前也去过嘛,舂苞谷稻谷这种,我们生产队在这里嘛。他们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嘛这样子,我们在他门前嘛,也不进去。但是如果觉得不注意,进去就进去了嘛没有关系,不进去就不进去,这样子嘛。”(0222YZL访谈记录)YZL大妈所说曾进去关帝庙的时期是六七十年代,彼时龙泉寺被用来作为生产队的打麦场,寺中所有神像包括关帝在内全部被毁。没有了神像的关帝庙,禁忌仍然存在,但出于生存所迫,女性也不得不进去庙中生产劳作。七八十年代龙泉寺内的所有神像逐渐重塑以后,YZL大妈没有再进去过,不过以前的经验让她相信进去了也没关系。 由上可知,从三国演义中关羽忠心护主的事迹,到关帝不喜欢女人的联想,再结合一个女人因为进入关帝庙而死亡的故事,由男性讲述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传说似乎建构了一个针对女性的禁忌。鉴于关帝庙及其所在的龙泉寺在人们心目中,是比村中其他神祇地位更高的“大神大圣”所在地,同时又是以全村老年男性为主要会员的宗教组织洞经会的活动场所,女性的禁止入内应是宗教观念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双重限制。但渐渐深入调查,笔者发现,村中拥有故事讲述特权的男性自己解构了由这些故事建构起的禁忌:首先,他们认为关羽不喜欢女人的传说只是人的一种说法,女人因进去关帝庙而死的故事不太真实;其次,他们觉得女人进去关帝庙会得病是女人自己的心理作用;最后,他们认可“干净”的老妈妈,以及被视为“小娃娃”、“大学生”或者“本心无愧”的笔者进去关帝庙中。 然而,作为这一禁忌对象的村中女性,她们并不了解关羽不喜欢女人的故事前因,也无法确定一个女人因进去关帝庙而死亡的故事是否真实,只知道“他们说去不得”以及“去了会得病”。这里的“他们”既是传说,又是所有男性和其他女性所构成的舆论,加上对身体病痛的想象,强化了女性的自我约束,构建了女性无法被解构的禁忌。这一禁忌已然具有了另一种生命力,被村里的女人们忠实地恪守,并以此教育年轻的女孩们,不论是小娃娃还是大学生,只要身为女性都一视同仁为禁忌的对象,即便是曾进去过关帝庙,并认为进去没有关系的女性也不再进去庙中。由此可见,似乎并非是社会强夺了女性的某些自由,而是女性自己限制了自己。 四、结语作为波伏瓦对女性是存在但非本质论述的哲学思想源泉,萨特的存在主义论承认所有人都是处在一个有组织的无法摆脱的处境中,但是同时认为这些限制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客观是因为有人在这些限制下生活,而如果没有人在这些限制下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人不联系这些限制而自由地决定自己和自己的存在,这些限制就是毫不足道的。”[21]因而,“决定我们存在的是我们自己。”[22]从这一层面讲,萨特的存在主义对今天如何看待女性受压迫问题仍然有重要意义。 过去的几十年间,周城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政策的保护以及国家的重视助益了周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由上述两个故事的变化可以看出,针对女性的外在贬抑的社会观念已然改变,这与周城村近百年来的变化不无相关。作为中国最大的白族聚居村庄,传统上的周城重男轻女思想的确十分严重。生了男孩家门外会贴“弄璋之庆”,而生了女孩则贴“弄瓦之庆”。周城历来地少人多,农业耕种十分辛苦,和男性一样,妇女也需要上山砍柴,下地劳作,除此之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是妇女的分内之事。即便如此辛劳,女性的社会地位也一直很低。受近百年来的思想解放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现代国家对女性地位的重视,周城村一些陈规陋习被破除,女性受教育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观,年轻女性得以脱离父母包办的婚姻。改革开放后,凭借具有民族特色的扎染和服饰,周城妇女为家庭和整个村庄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 流传于周城的三个故事从侧面为上述女性地位变迁提供了观照,并在集体记忆层面反映出社会观念对女性看法的转变。在母猪龙传说中,女性被隐喻为妖怪,需要有宝塔镇压才能顺服,但故事渐渐不被人们信服并淡忘,女性在婚恋上的主动与服饰上的自由得以为社会接纳和认可;两位娘娘的故事中,被男性捆锁的女性被除去了锁链,被改写为男性的追求者,体现了社会观念对男性行为的限制和女性地位的尊重,女性一定程度上不再是男权社会中的被动者;而在关帝庙的故事中,男性解构了由他们讲述的女人不能进关帝庙的故事,可见外在的社会观念对女性的限制并非没有缺口,但同时女性却为自己建构了另一种禁忌,这一禁忌并非由一套叙事逻辑建构,而是女性畏于“他者”的看法和对身体疼痛的想象,即对自我的主动束缚。 至此可以看出,现代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地位在社会经济方面与思想观念上都有显著提高,使女性无法自由移动脚步的,早已不是外在于女性身上的限制,而是被女性主动内化的道德约束,女性并非是“受压迫的女性”,而是“自我束缚的女性”,传统社会要求她们的外在社会规范已经化作了她们自己的内在道德诉求,女性充当着“一半是受害者,一半是同谋”[23]的角色。来自外在的锁链可以通过外力废除,而隐藏的锁链却令人无计可施,如何除去隐藏在女性心中的锁链,才是现今谈论男女平等和女性自由的关键。 注释 [1]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概念,本文参考叶文振等人的《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人口学刊》,年第5期),指“女性或作为一个个人主体或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被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尊重程度及其所拥有的生存与发展机会的平等程度”。如果一个女性不仅在社会上受到良好的人格尊重,同时拥有与他人同等的社会参与机会,那就可以表明她处于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 [2]沈海梅:《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3]沈海梅:《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4][美]许烺光:《祖荫下》,王芃、徐隆德译,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年版,第-页。 [5]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序),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年版,第1页。 [6][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第5、页。 [7]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序),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年版,第3页。 [8]周城村位于云南大理古城北23公里处,笔者于年1-2月、7-8月,年6-10月,年10月—年6月四次共13个月的时间在此地进行驻村田野调查。作为“中华白族第一村”,年周城总人口达人,其中白族人口占98%,因地少人多,且靠近著名景点蝴蝶泉,主要经济发展方式为依靠旅游业带动商饮与服务业。本主崇拜(兴起于公元年左右、集原始崇拜与人物崇拜为一体的民间信仰)作为大理白族的普遍信仰,也是周城村民的信仰特色。 [9]周城村的名人和知识分子,段凌云是清朝光绪戊戌(公元年)贡生,杨上培是清朝光绪乙酉(公元年)举人。 [10]据村民说,最初人们只知道这尊本主是一个打猎匠,后来所称的“杜朝选”一名是村民在关帝庙(圣谕堂)前扶乩而得。 [11]李星华:《白族民间故事传说》,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年版,第38-43页。 [12]根据武汉大学朱炳祥,徐嘉鸿、陈鑫、李慧采访录音并整理的《周城文化习俗》(,未出版),第60页。 [13]郝翔、朱炳祥等《周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14]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5]朱炳祥:《一个文化变迁的斜向结构——周城“蟒蛇共蝴蝶”文化现象的田野调查及分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 [16]蝴蝶泉的传说还有郭沫若创作的另一版本,主角是雯姑与霞郎,但当地人都称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故事,这是作家个人的文学创作,与能体现集体记忆的当地民众集体创作的传说故事不同,故不予讨论。 [17]根据武汉大学朱炳祥,徐嘉鸿、陈鑫、李慧采访录音并整理的杨宗运口述《周城文化习俗》(,未出版),第65页。 [18]洞经会,是以演奏洞经音乐为主要祭祀手段,儒道佛色彩皆很浓厚的宗教组织。直到年以前,周城洞经会的会员全部为老年男性,以后才开始陆续接纳女性会员,即便如此,截止到年八月份,现有名的会员中仅有13名女性。 [19]由方广会和莲池会合并而成的宗教组织,方广会会员为老年男性,信奉观音老祖,以《方广经》为经典;莲池会会员为老年女性,信奉观音老母,以《莲池经》为经典,为方便管理,方广和莲池合并为方广莲池会,并根据地域划分为南方广莲池会和北方广莲池会,其中方广会为大,南北方广莲池会的会长均为男性。 [20]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中的确讲述曹操想要破坏关羽与刘备的关系,“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而民间流传当时关羽夜读春秋,《三国演义》中则无此说。 [21][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第22页。 [22][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第17页。 [23]让-保罗·萨特语,转引自[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第1页。 作者简介:杨雪(-),女,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原文来源:《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1辑。图片来源于网络。 赞赏 长按网络HR文员北京白癜风治疗哪家医院好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中国民间故事丛书云南玉溪江川卷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